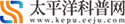
引: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少夫人,这都是少爷的意思,他让我来诱骗你……
*
传说在日本平安时代,是一个人类和妖怪共同生活的时期。在那个年代的京都,每到夜晚街上都空无一人,这时候各种奇奇怪怪的妖怪会陆续出现,像是庙会一样在街上游荡……
^_^本系列是引用《百鬼夜行》里的原型,架空写的故事哦,背景是我国古代哈~
百鬼夜行の屏风窥
翠帐红闺中,一对情人恩爱缱绻,立下誓言:“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做连理枝。”可最后男子变了心。被背叛的女子心中满是怨恨,在曾经的红闺中整日哭泣,痛骂男子的薄情寡义,这一切都被七尺屏风看在眼里,浓浓的怨念使它化成妖怪——
*
“湄娘,绝不能让那青楼女子进我们袁家的门!”缠绵病榻的婆母已甚是憔悴,但语气却分外坚定。
“您放心,我知道的。”她点头应声,顿觉如芒在背。那双曾给过她脉脉温情的眼睛,此刻竟射出利刃般的目光,直刺心间。
她放下帷幔,叮嘱丫环好生伺候之后,悄声退了出来。袁思然阴沉着一张脸,抢步上前,一手撑在廊柱上,挡住她的去路。
“你别想用娘亲的话压我,姈奴我非娶不可。正室又如何,不过一纸休书的事!”
她抬起头,在袁思然的瞳孔中看到自己苍白单薄的身影,宛若一片纸屑,幽幽坠入旧梦的尘埃。
弃捐箧笥中,恩情中道绝。
“思郎,那个姈奴究竟好在哪?”她最后一次这么唤他,甜蜜柔情的呼唤,竟能变得如此苦涩。
“还用说吗,自是什么都好。”提起那狐(媚)撩人的女子,他唇角勾起得意的弧度,言辞间还不忘鄙夷:“燕雀岂知凤凰之姿?”
“即使她在你带回来的糕点里放了红花,让我没了孩子……也都无所谓吗!”她忍不住低泣着轻喊,泪眼朦胧中,她看到同自己定下白首之约的男子一点点地破碎。
“给我闭嘴,口口声声说姈奴卑贱,自己却用更卑鄙的手段污蔑她,你真以为我不敢休了你!若不是你、呵,其实是你故步自封,自以为技艺高操。”袁思然冷笑着扬眉:“殊不知这天下第一的绣艺,早已不是你了。”
让袁思然诧异的是,她并不像想像中那般勃然色变,也没有追问那人是谁,依旧一副倦怠悲寒的神情:“你执意为之,我也无甚可说,只是进袁家后,我答应了婆母两件事,第二件既无法做到,那第一件便誓要做到,也不枉婆母和我母女一场。”
“待我绣成百花梦蝶瑰彩卷,你再让那人进门。”
姈奴折断了手中的玛瑙簪,炫目的阳光从窗格照进来,掌心仿佛两道凄艳的血痕:“她要是十年八年、一辈子都绣不成呢!让我躲在这角落里耗尽青春,直至油尽灯枯也不能名正言顺,真真是杀人不见血……”
袁思然看着玫瑰泣露的娇媚佳人,痛怜不已:“姈儿放心,我也不回府了,在这里陪你。”
“这怎么行呢?姈儿怎能让相公背上不孝的骂名……”姈奴握着袁思然的手,晶莹的泪珠落在他指尖,思量了一会后,又嫣然而笑:“相公,姈儿想到法子了。”
蓝田很喜欢姈奴,若说喜欢到什么地步,他觉得如果需要,他愿意为姈奴付出性命。
可惜,他只是锦鸾绣庄的一个绣工,姈奴并不需要他的命,连钱也不需要。
姈奴是青楼的花魁,卖艺不卖身的牌子在雕花扇窗上挂了七年,任多少风流富少、纨绔子弟争相追捧、一掷千金,也没能摘下。更难得的是,她的美貌仿佛有魔力一般,数年如一日的妩媚(妖)娆,碧波横流、胭脂唇勾,小小的动作便是万千风情,故追捧她的男子从未有过厌倦一说。
花魁如此,引得城中男子迷恋、女子生怨,姈奴却巧笑倩兮,说自己的牌子并不难摘,只有一个条件。
“娶我。”
十年一觉扬州梦,赢得青楼薄幸名。
众客人来青楼无非是寻欢作乐、醉生梦死,一掷千金的潇洒、花前月下的浪漫、清歌妙舞的迷醉……即便落得薄幸名声的调侃,也都是风流一种,但娶青楼女子回家,那真是个天大的笑话,谁也不会那样傻。
邂逅之前,蓝田一直听说着姈奴的故事,倒不是他冥冥之中已预感到这段缘分,而是因为绣庄的绣娘们太爱嚼舌。
“知府的公子昨夜也捧了姈奴的场,甩手就是一袋金锭。”
“都说她的眼睛能(勾)人呢,被盯上就逃不了,鬼迷心窍似地朝陷阱里扔钱。”
“不是说她时常到山里去拜狐仙么,怪不得一副狐(媚)样子,勾(魂)摄(魄)的……”
她们嫉妒而不甘,甚至可以说是痛恨,原因很简单,她们终日辛劳地做着绣活,以至眼睛昏花、手指酸痛,一个月下来也不过几两银钱,而那青楼女子一颦一笑间,便是她们整年的血汗钱,如此天悬地隔的差距,使她们即便素不相识也照样恨得铭心刻骨。
不过任她们如何夸大其词,蓝田也并未沾染上怨气。他秉性素来清和恬淡,不可能莫名去憎恶一个女子,而且他极有刺绣天赋,热衷在丝绸锦缎上绘绣出一幅又一幅美丽图卷,并非当做谋生的活计来敷衍甚至煎熬。
他和姈奴的缘分,便始于刺绣。
那天,一乘粉缎小轿停在绣庄门前,丫环还未及掀帘,已是一阵袅袅幽香。下轿的女子一袭红裳,媚而不妖、艳而不俗,一双美眸宛若浸润在天河中的星辰,熠熠生辉,让人移魄忘魂。
掌柜看得恍了神,一时分辨不出是富家千金还是豪门贵妇,迭声吩咐伙计奉好茶、呈绣样。
“这些绣样都是我们最出色的师傅绣的,您看看喜欢哪种式样?”
女子仔细看了一番,最后将那玉葱般的手指点在一幅缎绣上,蓝田日暖玉生烟。
“这位师傅在吗?”娇喉盈盈,宛若空谷莺啼。
蓝田被伙计找了过来,他隔了几步站定,任是低着头,也觉那明媚的光亮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
女子让丫环付了两枚金锭,一双美目凝着蓝田:“还请师傅明日到家中一叙,我好细细告知刺绣所需。”
“好,不知姑娘想绣何物?”
“嫁衣。”
“你们听说了没,这回真被那姈奴钓到乘龙快婿了,就是彩凰绣庄的袁大少爷!据说被她迷得神魂颠倒,立誓要娶她呢,现已为她赎了身,安置在城郊的宅院,真是家门不幸!”此话一出,绣娘绣工们一片啧啧声。
“不过啊,袁夫人坚决不同意,而且彩凰绣庄全靠着他家少夫人的绣艺,才得以坐稳城中第一绣庄的位置,于孝于利,袁少爷这么做都太傻了。”
“怎么说呢,只能说姈奴拜了这些年的狐仙,终于显灵了……”
蓝田在一片酸言恶语中收拾好绣品和针线,向掌柜打了招呼,按女子给的地址寻去。
城北以北,是城郊吗?他心里过了一过,却不愿多想,直至来到宅院,见仆人们正在挂灯笼,红灯笼上赫然写着“袁”字。
蓝田也说不清自己是何心绪,只觉唇角泛起一丝寥落的笑意,说来也是,那般妩媚绝色的女子,才当得起追捧与嫉恨的花魁之名。
初夏的熏暖天气,姈奴在家并不盛装,只着了一件珊瑚色锦纱裙,如墨的青丝才洗完,似瀑布般披散着,绸缎般的光泽,依稀可见人影。戴着双环玛瑙镯的皓腕轻轻一晃,红晕顷刻迷了蓝田的眼。
“我和相公好容易才修成正果、结为夫妻,故我想请天下第一的绣艺师傅为我们制喜服。”
“承蒙姑娘赏识,我定会尽己所能做到最好,只是这天下第一的绣艺,我实不敢当。”蓝田拱手道。
姈奴闻言,樱唇一撅,于冶丽妩媚中露出几分娇俏,蓝田的心弦仿佛被她的纤纤玉指撩拨着,意乱(情)迷。
“师傅为何如此谦逊,别因那些大绣庄的名头减损志气,你的技艺比起彩凰绣庄的镇店之宝,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姈奴让丫环拿来画轴,将画卷在桌上展开:“这是我绘制的龙腾祥云和百鸟朝凤,请师傅依着图样刺绣。”
蓝田早已为姈奴的美貌所倾倒,看了画卷后,更是被她的才情所折服,回过神后忙深深点头:“姑娘放心,我定潜心竭力,不枉姑娘这精湛的画技。”
此后,蓝田每日都去城北的宅院,为姈奴缝制嫁衣喜服。姈奴特意给他布置了一间静谧的房屋,推开扇窗,便可看到香薰草暖的后花园,她在那抚琴作画、赏花散心,一举一止,皆成风景。
有时候,还看到她和袁家少爷花前对饮、月下共语的恩爱情景。他心里不由感慨叹息,此等如花美眷,却被世俗所伤,只能躲在方寸角落里相守,不能正名。
一见倾心,再见倾情,可我除了绣艺,什么都给不了你。只盼早些为你绣成嫁衣,做世间最美的新嫁娘。
然而,半个月后,姈奴忽然来到他房里,美玉般无瑕的脸庞上,泪痕斑斑。她看着快完工的瑰艳嫁衣,美眸倏然一痛,玲珑身姿宛若被折断的花枝,颓然跌坐在地:“为何这样待我……我究竟做错了什么……”
“姈奴姑娘,不知出了何事?”蓝田心疼不已:“我若是能帮上忙就好了……”
于是,蓝田被袁府的家丁引着,进入内院,去见那个辱蔑姈奴尊严和爱情的女子。
“百花梦蝶瑰彩卷,是袁家传了几代的梦,蓝师傅若不相助,她是断不可能成功的。”
“可是,绣花引群蝶,这殊绝的技艺,我也没什么把握、”
“蓝公子!还望你为姈奴试一试,好么?”姈奴泪光冰莹的双眸、柔媚的央求,即便再多烦难,他亦随之点头。
蓝田心之所想皆是姈奴,见到袁少夫人时,耳边仍萦绕着她的啜泣与央求,不由皱起眉头。
“少夫人,这是如今城中最有名气的绣工,蓝师傅。”家丁介绍道。
蓝田这才回过神来,意识到自己面色不对,担心会露出破绽,妒妇的窥探本事素来犀利,对此他甚为了解,连忙一改神色,敬重地抬头。
谁知,女子根本就没朝他看,而是低头理着绣架上的数十色丝线。
“少夫人、”
“我知道了,你去吧。”女子的声音清浅低迷,似山谷间快要流尽的泉水,幽咽泉流冰下难。
蓝田静默着等她开口,隐隐觉得气氛有些不对,自己对她固然带着成见,而她,对自己似乎也并无好感,清瘦的身体一直侧对着他。
“你的技艺是在锦鸾绣庄所学?”
“是的,少夫人别看我们绣庄名号不够响亮,其实我们、”
“不,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女子摇摇头,轻叹了口气:“你用锦鸾绣庄教的技艺,为我们彩凰绣庄效力,这样……好吗?”
蓝田愣了愣,原来她顾虑的是这一层,或许撇开情事,她是讲理且知礼的人。
“我最初的技艺确实是绣庄师父所教,但这几年的刺绣针法,皆是我自己所创,师父说我随时都可以出师,因此您不用担心。”
女子微微颔首,却依旧若有所思:“可是绣成之后,对你的声名会减损吧,少爷将你介绍过来,是顾不上我们绣庄的声誉了,你呢,也不怕陷入忘恩负义的流言吗?”
“少夫人不必多虑,绣品以你之名便是,我不过是个帮手,难道还要求像名家作画那样题上落款不成。”蓝田斟酌片刻,便即刻答道。此前他还真没思量过这些,姈奴宛若他平淡生命中蓦然出现的一道虹光,绮丽绚烂间,他已忘却所有世俗烦忧。
为了那道虹光能永远绚丽,他愿意在平凡寡淡的日子里继续,只要能偶尔看到她的如花笑颜,足矣。
“这怎么行呢?不属于我的,我不能要。”女子摇头回绝,打断了蓝田的思绪。
“无妨的,还请你千万别介意,因为、我也是有所图……”蓝田着急起来,生怕女子不答应。细想之下,百花梦蝶图会不会是她的计策,让姈奴陷入漫无尽头的等待?
女子似感受到蓝田的痴情,苦笑道:“为何都这么傻,不过最傻的、还是我……”
她摇摇手,示意不想再听蓝田解释:“方才家丁说你叫、”
“在下蓝田。”
“蓝田,既是如此,那就开始吧。”女子转过身,郑重地同他点了个头,像朋友间的合作、高手间的过招。
蓝田有些愕然,他从未被这样对待过,是低贱的手艺师傅,难得获有的尊重。
他赶忙回礼,抬头后才正视她的脸,目光不由停了一停。
她比自己预想的更年轻,也更美丽,眉梢眼角皆不见嫉怨之色,而是一种黯然的哀愁,紧颦的黛眉下,深潭般的眼眸旋着漩涡,望得久了,只怕会对她的情愫感同身受。
蓝田将目光收了回来,自己已被虹光所迷,没有心绪去看那潭水中的暗影。但心底却忍不住叹息。
她不是被折在瓶中的花枝,静待凋谢;也不是被绣在屏风上的花案,身不由己;而是被遗忘的鬓边花朵,忧伤失落中,仍摇曳着温柔轻暖的情意。
蓝田揉了揉眉心,几十色的丝线在眼前纠缠缭绕,他急需一片素净的云。
女子一袭水色丝裙,临窗而坐,为了方便刺绣,她髻间腕上皆无半点佩饰,墨发用手绢挽着,露出下弦月般的清瘦侧颜。
思君如满月,夜夜减清辉。
这朵鬓边花散发着幽幽残香,再相处下去,自己只怕会愈加同情她……他深呼了口气,急忙打消念头,提醒自己要保持警惕。这世间因怨生恨的故事太多,而这女子的所作所为,又十分矛盾。
她不愿让袁少爷娶姈奴,便许了个难以实现的承诺,为难他们。可现下,她又分明在为这个承诺努力,孜孜不倦、心无旁骛。
“怎么,你有什么心事吗?”日色西沉,她放下手中的绣花针,揉捏酸疼的手指。若说她身上有什么色彩,便是那常年执针的指尖上,点点朱砂红痕。
“哦……”
“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田日暖玉生烟。你是不是,有个叫‘沧海’的兄长或姐姐?”
他闻言,眼中平静的池水氤氲起烟雾,于心底泛起隐痛和感动:“嗯,我有一个孪生姐姐,蓝沧海……十年前家乡水灾,只有我、活了下来。”
她没有即刻回言劝慰,反而起身走到门边,唤来廊下的丫环:“你去厨房,让澜城的徐厨娘做一碗莲叶羹。”
蓝田听到她说起自己的家乡,眼泪终于冲出十年的尘封岁月,汩汩而落。
“谢谢你……”熟悉的甜香从舌尖漫延至心间,在羹汤升起的袅袅薄雾中,他仿佛坐上儿时温暖无忧的小舟,重温旧梦。
晚霞倾泻而下,房内的绣品皆漫上红光,唯她那水色丝裙,依旧澄澈无瑕,不染纤尘,他看着她指尖的血痕,轻声问道:“你怎会想到这些,莫非你也是以诗为名?”
“嗯,我姓伊,叫伊湄。”
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
蒹葭苍苍,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,在水之湄。
“我爹和我娘自小指腹为婚,故连名字都取得应景。我爹叫伊水,我娘叫蒹葭,我还没出生的时候,爹就想好了名字,男孩叫伊方,女孩叫伊湄,这样我们一家人的名字都在一句诗里。”
“可我娘身子弱,不该有我的,但为了情爱的延续、为了伊家绣法有人承袭,她拼上了自己的性命。娘临终前,爹向她承诺,我虽是女孩,但他此生也绝不会再娶,将我抚养长大后,就同她团聚。”
“我十三岁那年,本就久思成疾的爹愈加病重,他让我别难过,是因为他和娘彼此都等得太久,迫不及待地想重逢。我和袁思然的婚事,只是爹和故交袁老爷的口头之约,而且那时袁老爷已经去世,爹给袁家去信,不过姑且一试,没想婆母和袁思然很快就赶了过来,婆母承诺会待我视如己出,袁思然说他对我一见倾心,定会相守一世。这两份承诺,让我爹安心阖目。”
伊湄唇畔牵起一抹哀伤的笑意,眸中苦涩漾漾,蓝田正担心她若继续诉苦,自己怕是会陷进那湾幽柔苦涩的溪水中。然而,她却转了话锋,开始劝慰他。
“‘你好好活着,便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’这是我爹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,你的亲人,定也如此。”她点燃他身旁的座灯,橘色的暖光徜徉着:“所以,不用刻意把故去的亲人尘封在心底。不敢追忆,他们和你同在……”
蓝田感动而疑惑,不解伊湄为何如此暖心地劝慰自己,在苦涩纠缠的情事中,自己分明站在她的敌对边。
“是不是觉得我太多话了,因为我想把伊家绣法教给你,遂和你说、”
“咚——”廊外好像有人磕了一下,蓝田稍稍唬了一跳,伊湄却黯然沉下脸,不再说下去。
“公子,快去看看我们小姐吧!”这日,蓝田才出袁府,便被姈奴的丫环拽住衣袖,焦急地往城郊赶。
丫环哭哭啼啼地告诉他,这段时日袁少爷很少到宅院见姈奴,总是推说绣庄和商号有事,姈奴本就觉得“百花梦蝶”是一场无望的等待,现下更是担忧袁少爷会变心,整日以泪洗面,伤心欲绝。
“小姐这两天总是看着嫁衣恍神,茶饭不思,公子你快去劝劝她吧……”
姈奴一袭嫣红嫁衣倒在地上,宛若一枝秾艳绚丽的玫瑰,润玉凝雪的脸颊苍白而绝望,晶莹的泪痕闪着破碎的光,美得让人移不开眼,心疼得让人忘了呼吸。
“姈奴姑娘、姈奴姑娘,你千万别想不开。”蓝田看着美人凄绝图,疼惜不已。
“蓝公子,姈儿等得好痛苦,姈儿等不下去了……”姈奴似见到亲人般,抓住蓝田的手臂,泣不成声。
蓝田心下哀然,这枝被袁少爷折断的花枝,只能送到他手中,让他悉心疼爱呵护。至于伊湄,她潜心于刺绣,不像姈奴这般一无所依,应该还好吧……真的好吗?
迟疑间,蓝田不由皱起眉头,耳边响起初见那日,伊湄叹息的问话:“这样好吗?”
“蓝公子,怎么了?可是嫌姈儿烦?”姈奴抽咽着,桃花眼又氤氲出两颗泪珠。
“怎么会呢。”蓝田急忙摇头:“姈奴姑娘放心,伊、哦,袁少夫人极有刺绣天赋,现已将‘百花梦蝶’的丝线配色和针法钻研出了头绪,我也在竭力帮忙,这梦蝶图已不再只是梦了。”
“真的么,这可太好了……可是,她当初的话还算数吗?会不会只是个计谋?”姈奴揪紧蓝田的手臂,娇声问道:“她是不是想着,完成了天下第一的绣品,袁家绣庄商号就全仰仗她的声名,相公便不敢再留恋我这卑贱的烟花女子?”
“我看她品行挺好的,应该不会食言吧,你若是不放心,我再去问问她。你别再忧心伤神了,好好养病,还要做最美的新嫁娘呢。”
姈奴听话地点头,于泪眼朦胧中绽出桃花含露的柔媚笑容:“蓝公子真是姈儿的贵人!”
“你之前说的话……作数吗?”
“作数啊,不作数又何必说呢。让她进门是真的,还有教你伊家绣法的事,也是真的。”伊湄剪断手中的丝线,淡淡一笑:“是不是觉得很矛盾?”
“其实也没有什么,我答应了婆母,钻研伊家和袁家绣法的精髓,绣出百花梦蝶瑰彩卷。这是他们几代人的心愿,宿愿既成,对于袁思然娶青楼女子的瑕疵,她便不会太在意吧。还有你,即便是为了姈奴而来,但你天资和品行都好,是可以传承的人,就该教于你。”
轻暖的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,她抬手理着绣架上的丝线,蓝田看着那双纤纤素手凝神,她所绣出的花样,只怕能将城中布满锦绣绮云,而她自己,却素净悲凉如雪絮,守在这寂寞的方寸之地。
她不像姈奴,娇声软语,流着让人心恸的眼泪,她脸上的晶莹,是鬓角的那星汗珠……他看得久了,恍惚陷入一种空茫的隐痛。
伊湄幽幽叹了口气:“待学完伊家绣法,你先离城避一避吧,不论怎样惦念姈奴,也等上一年半载再回来,介时,是走是留,你自己再决定。”
“这、有什么缘故吗?”
“因为你没有受过情的苦,怕你在懵懂中,落得个粉身碎骨……”
蓝田诧异而困惑地看着她,她却不再做任何解释,仿佛已经言尽。在这场情怨纠缠中,她陷入痛苦煎熬、姈奴陷进风雨飘摇,自己不过一个帮手,为何会被用及这样严重浓烈的字眼?
“伊湄,你对姈奴可能有些误解。”他自己也觉得此话不妥,声音轻似微风。
“也许吧,但就现下来看,你对她的误解更深些。”她浅涩一笑,眸光渟渟。
蓝田忽然想到,从相识到现下,她眼中的神情都是淡泊的,或清冷悲寒、或哀伤惘然,都是轻轻浅浅,从未有过浓烈的色彩。就此看来,她并未准备对付姈奴,那“粉身碎骨”的警醒,却是因何而起?
“别想了,来绣花吧。”她将配好的丝线穿进绣花针,绮丽鲜艳的色泽,在素白的指尖绵延,宛若寻梦的灵羽:“千针万线,情意交织,刺绣最重要的一点,是别把怨情与恨意绣到瑰丽美好的图卷中。”
花随玉指添春色,鸟逐金针长羽毛。
我们刺绣,是为了让人间美景更长久,而不是让怨恨漫停留。
“玫瑰由你来绣,我怕我会忍不住让它沾上寒意。”她将另一支银针递给蓝田,针眼已穿入她配好的丝线,绚烂的嫣红、浪漫的绯红、迷醉的霞红,再和着灼灼的金色,他心里的玫瑰,正是这个模样。
他执着银针,潜心绣了起来,她也低头去绣另一边的芙蕖,不再言语。一时间,绣房内静得只剩下丝线细微的穿梭声,和她那轻浅的呼吸,漾着疏疏落落的馨香。
这默然的相处,与姈奴相对时完全不同,她不会撩拨他的心弦、摇撼他的情愫,而似一泓幽柔沉静的池水、一阵清婉恬宁的馨香,缓缓将他浸没、引他入梦,点点滴滴、丝丝缕缕,水滴石穿、柔香沁骨……
“除了玫瑰,还有一种花我能绣好。”他抬起头,看着她弦月漫霜的侧颜:“我的家乡有一种花叫九里香,也叫过山香,花朵腻白如玉、花株幽美秀逸,最妙的是,悠远的香气能绵延过山。翻过家乡的山峦回望的时候,那缕花香,是最深的眷恋。”
“伊湄,我觉得,你就像那温情馨宁的过山香。”
百花梦蝶瑰彩卷完成的前夕,她第一次扯住他的衣袖,贴在他耳畔轻语:“今夜就走,别让任何人知晓。”
轻柔的语气,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
仓促与失意间,他连行囊也没准备,只带着她用绢帕裹的几枚银锭。她绣了无数的锦缎绫罗,可绢帕上却无半星花样,一方素净的水色,真真是所谓伊人,在水之湄。
她似看出他心中所想,空茫一笑:“这世间再怎样绚烂缤纷、五彩斑斓,可最后的最后,也只剩素心一片。”
那天,艳阳高照,蓝田走在喧闹的长街上,一抹红霞、一湾素水,在心头纠缠萦绕,前所未有的纷烦与寂寥。
“听说了没,那个姈奴终于得逞了!”
“可不是么,色令智昏的袁少爷带着她到彩凰绣庄,大张旗鼓地量制嫁衣,真是不知羞耻!”
“可惜了袁少夫人……”
他猛然想到了什么,心倏地一震,娶为妻,纳为妾,姈奴所说的娶,并不是爱情修成正果的圆满结局,而是、践踏在他人痛苦与尊严上的可怕私欲。
“姈奴莫非是、要让袁少爷休妻?”他颤声问闲话的妇人。
“呵,就那恶女人,只怕会比休妻更毒、”妇人摇摇头,本还想继续说,却被旁边的同伴推了一把,想是疑心蓝田曾是姈奴的客人,不愿招惹是非。
蓝田只觉心里堵得难受,急忙往回赶,他冲进绣房时,伊湄堪堪剪断“百花梦蝶”的最后一根丝线。
前几天就可以绣成的,她却等到现下,是为了让自己走得更远么?
“你回来做什么!”她幽湖般的秀眸中,第一次有了浓墨重彩,是焦急与痛惜。
“因为他傻呀。”依旧是婉转娇喉,丝丝如媚,此刻传入耳中,却阴暗似鬼魅。
姈奴一袭艳红嫁衣,宛若缠枝玫瑰般依在袁思然身侧,娉婷而来:“相公,姈儿的主意妙吧?”
“是啊,姈儿最聪明了,让我一劳永逸。”袁思然抬手勾了勾姈奴的红唇,和她一同笑了起来,张扬恣意、满怀恶意。
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,要做正妻是吗?那就赶紧写休书,我带伊湄走便是。”
“当然是你带她上路啦,否则我们这场局不就白设了。”姈奴媚眼一撩,见蓝田仍未会意,便耐心解释道:“彩凰绣庄全城第一的声誉要紧,怎能让你们出去自立门户?再说了,一纸休书固然容易,却后患无穷,我可不想让相公背上薄情寡义的骂名。”
“最最重要的是,根据我朝律(法)、”姈奴巧笑倩兮,眼中寒星似毒舌吐着信子:“夫婿若撞见妻室(奸)情,愤怒之下杀(奸)夫(淫)妇,无罪。”
“你……”蓝田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子,这朵曾让他惊艳(勾)魂的绝美玫瑰:“太可怕了……”
“何必呢,你们放一把火岂不是更简单,本就是无中生有的事,在废墟里给我捏造个(奸)夫,也不是什么难事。”伊湄拂去裙摆上沾着的断线,从容道:“你们也知道,他是天下第一绣艺,这么杀了多可惜。不如留他一命,像我从前那样,为绣庄维持声誉。”
“哼,你说得轻巧,他都知晓我们的计划了,怎能留活口。”姈奴嗤声道。
“这有何难,他本就被你迷得失魂落魄,让郎中开几副散神药,你再哄一番不就行了。”
姈奴思量片刻,对袁思然道:“相公,蓝田的事我们再想一想,先给她个痛快吧,免得夜长梦多,让下人看出端倪。”
“罢了,我留你个面子,就说是自尽,免得你变厉鬼,我还得找人驱邪。”袁思然抽出早已备好的长剑,向伊湄刺去,谁知,本有一线生机的蓝田竟飞身过去,挡在了她身前。
剑刃先穿过我,再刺向你,这样,是不是多了分温暖,少了分痛楚?
“你为何、”
“为何回来吗,因为你啊。”他侧头向她微笑,温情缱绻:“玫瑰只是一时惊艳,过山香则是心中宿愿,一生依恋、永远眷恋。”
血汩汩而流,两人的生命仿佛融在了一起,他用最后的力气,将染着两人血水的手掌一挥,血迹溅在百花梦蝶瑰彩卷上,一抹诡艳凄绝的红影。
彩凰绣庄终于完成了几代人的心愿,一幅“百花梦蝶瑰彩卷”,远胜繁华十里、万千美景。
袁家少爷和新少夫人特意请来全城最巧的工匠,用名贵的金羽红檀,将瑰彩卷制成屏风,摆在绣庄正中,成为新的镇店之宝。
众人纷纷慕名而来,看这瑰异灿艳、幻彩辉煌的绝美刺绣。争妍百花宛若在仙境中幽美盛开,引来百蝶翩跹共舞,如此殊丽奇景,让观者如进幻梦,惊叹连连。
彩凰绣庄自此声名大震,从全城第一升为天下第一。
“不错,这‘百花梦蝶’真是名不虚传。”这日,绣庄来了几位谈吐不凡的客人,说话的男子更是剑眉星目,眸光锐利。
“多谢公子夸奖,这是我们绣庄的镇店之宝。”
“绣工师傅呢?”
“哦、我们前少夫人她、”掌柜顿了顿,不忍说那苦命女子的污言秽语,只伤感道:“这幅刺绣耗尽她毕生心血,绣成之后,便香消玉殒了。”
男子留意着掌柜的神色,剑眉渐敛,再次转身细看屏风,惊见屏风一角隐隐的暗红。
“这是什么,快拿烛火来!”
“我们绣庄今日有事,闭门送客。”袁思然正好回绣庄,见此情形,即刻挡在屏风前,吩咐掌柜关店。
“你送你的客,我查我的案,不相干。”男子推开袁思然,袁思然还欲阻拦,已被男子随行之人按住肩膀。
于是,睽睽众目看着男子将烛火靠近屏风,那抹暗红竟如泣血般,滴滴答答地落下红泪,在地砖上流成一个“冤”字。
众人唏嘘不已,袁思然脸色惨白地跌坐在地,闻讯赶来的姈奴惊叫起来,旋即嘤嘤而泣:“相公,这是怎么回事?你不是说姐姐是羞愧自尽吗,莫非是你故意冤枉她,怪不得你每夜做噩梦呢,奴家早劝你……”
“你这该死的女人!”
*
袁思然和姈奴被判凌(迟)那日,城中百姓去彩凰绣庄,在屏风前祭奠那对冤魂。
“百花梦蝶”依旧绮艳瑰逸、璀璨斑斓,众人感慨叹息间,竟看见那抹血迹化出两只洁白蝴蝶,有灵性地和大家致意后,幽雅扇动双翅,舞向天涯——